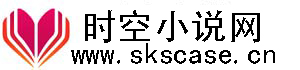13、死意(3/6)
淌。他看不到身后,但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他。那些目光像刺一样扎着他的背。他早已从神坛上坠落,从天之骄子成了他人茶前饭后的谈资。
一个人的脸皮到底有多厚,才能习惯被别人踩在身上的脚印呢。
连星夜手指不自觉地抽动,指尖是早已习惯的凉。
今天,楼照林没有牵他的手。
……
晚上,徐启芳搬了把椅子坐在连星夜旁边,等他泡完脚,让他把腿搁在她的膝盖上,一边给连星夜捏腿,一边检查连星夜的数学作业。
“你外婆让咱们周末回去吃饭,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多做点作业,周末好好陪陪你外婆,你外婆都好久没见你了,肯定想坏了。”
连星夜点头,表示自己知道了。
徐启芳低着头,没看见:“你的腿怎么好像越来越肿了,要不去医院看看。”
连星夜又摇头。他全身上下病得最轻的应该就是腿了,他甚至觉得这算不上病,除了楼照林那种用复习时间跑去打篮球的,学生坐久了腿上或多或少都有些水肿,尤其是脊椎,动一下就能咔嚓咔嚓响个不停,跟有声骨似的。可他身上的病只有腿上的看得见,所以妈妈也就只关心他的腿了。
人们无法凭臆想去判断一个人病了,只能通过这个人孱弱的身躯、苍白的脸色、还有肉眼可见的破损的肢体,这些外在的特征,得出这个人生病了的结论。
只有看得见的伤,才能算是伤。肉眼可见的伤痛总能轻易吸引别人的注意,能够让别人评判伤得多严重,才能让关心落到实处。然而人无法想象一种看不见的痛苦。看不见,就不知关心的举动该落到何处。无法给一种伤痛做评级,就不知该付出多少关心,只看那人笑着说没事,不用担心,久而久之,别人看他四肢健全,还有力气微笑,便真当他没事,再也无人关心,殊不知他的灵魂早已千疮百孔。
这也是为什么连星夜执着于在医院检查出个结果,他渴望他的伤痛被人看见。然而他连一份生病的证明都拿不出。
“怎么跟你说半天话都不吱声儿?我跟你说周六去外婆家,你听到没啊。”徐启芳抬起头。
连星夜连忙又点点头。
徐启芳把水端起来,皱着眉头埋怨:“最近怎么总是默不吱声儿的,本来性格就内向,再不说话,别人还以为我们家养了个哑巴。”
连星夜喉结酸涩地滚动,张了张嘴,努力想发出声音,徐启芳已经推门出去了,嘴里还止不住地嘀咕:“跟妈妈说句话都不乐意,母子俩搞得跟敌人似的,真是养了个白眼狼……”
不是的,他不是不想说话,是说不出话。他不是不想理你,只是发不出声音。
妈妈,别这么说他,他不是白眼狼,更没有想过要伤害妈妈……
随着妈妈温暖的气息离去,房间里最后一丝人类的气息仿佛也被带走。
连星夜早就不是人了,是腐烂物,是泥巴,是臭了水,巨兽捂住了他的嘴,不允许他和这个世界说话,于是他就被世界抛弃了。
他胸里堵着一口气无处发泄,于是烦躁地扇了自己几个巴掌,想起妈妈,还有自己那越来越差劲的成绩,又愧疚得嚎啕大哭。他像有多动症一样疯疯癫癫地爬下床,在地上走来走去,一边磕了药一样前后摇摆着身体,胸膛起起伏伏地喘不过气,他将冰冷的身体贴着墙壁,像粘液一样沿着墙一寸一寸地攀行,他没穿鞋子,脚底板冒出汗,黏腻潮湿的汗水粘在地板上,每一次抬脚都好像陷进泥巴潭子里,触感很恶心。
寒冷像涨潮一样从脚底一波波地涌上头顶,他每次都会猛地打一个哆嗦,浑身的鸡皮疙瘩抖